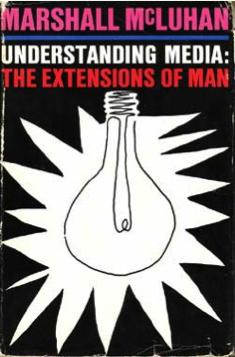
作者:蓬岸 Dr.Quest
知乎文章编号:308998277
创建于:2020-11-23 12:37:18
修改于:2022-06-30 2:30:26
目前中文世界里“平台研究”一词几乎被等同于“社交媒体研究”,而在两年之前我接触到“Platform Studies”一词时,平台研究的概念则更针对那些产生了创造性作品的硬件和软件的研究,两位相关领域的学者Ian Bogost和Nick Montfort在2009年的论文《Platform Studies: Frequently Questioned Answers》中解释了他们对“Platform Studies”的理解,以及一些常见问题的回应,本文即为其中文译文,供参考。
我们描述了关于平台研究的六个常见误解,它是数字媒体研究的一系列方法,侧重于研究那些支持创造性工作的计算机系统。我们对这些误解进行了回应,并澄清了平台研究的概念。
关键词
平台研究,平台硬件设计,技术学定论,社会建构主义,教育学,新媒体。
“平台研究”是数字媒体研究的一个新焦点,这是一套研究那些为创造性工作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方法。2009年,第一本从平台角度探讨创意数字媒体的平台图书得以出版:即我们编写的《与光线赛跑:雅达利视频电脑系统》(Racing the Beam: The Atari Video Computer System)[9]。这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平台研究”系列图书的第一册,而我们是这个系列的编辑。
Platform Studies, a book series published by MIT Press, Ian Bogost and Nick Montfort, series editors虽然平台研究直到最近才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其最早出现在2007年数字艺术与文化会议(Digital Arts and Cultures Conference)上——但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以至于被人们以各种的方式误解。我们本来的目标是为了回答数字媒体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但最后却常常遭到一些在我们看来忽略了平台研究项目意义的质疑。这些误解的详细引述,其中许多是通过私下的途径告诉我们的,而且更像是某种攻击而非帮助。为了推进平台研究的深入,本文回顾了对这一新概念的六种误解。我们将这一具有巨大潜力的,平台层面的新的关注点和这些误解进行了对比:
误解一:平台研究是技术决定论的。
平台研究反对“硬性”的决定论,并引导我们以一种生产性的方式打开技术的黑盒子。
误解二:平台研究是关于硬件的。
平台研究同样也研究软件平台。
误解三:平台研究只针对电子游戏。
平台研究将会扩展到所有产生了有趣的创造性工作的计算机平台。
误解四:今天的一切都是平台。
我们希望关注的是计算平台,这是数字媒体工作的基础。
误解五:平台研究针对的是技术细节而非文化,
平台研究将技术细节与文化连接起来。
误解六:平台研究意味着每个在数字媒体领域的人都需要受到计算机科学的训练,不然就会被排除出这个领域。
平台研究显示了对技术的理解是如何带来新的见解的,但这并非排斥数字媒体领域其他重要类型的学者。
通过我们对平台研究的概念的澄清,并解释了它如何对相关领域做出贡献,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做平台研究的工作,并使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具有吸引力。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评论能够推动对平台研究概念的讨论,以及对平台研究方法实质性、有成效、有针对性的批评,帮助这一领域工作的发展。
技术是否只循着自己的发展道路,直接地影响社会,而不需要社会的中介呢?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技术决定论”描述了那些认为技术对人类社会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理论和社会学方法。当代大多数的用例都对其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改: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变化受技术的影响比受其他来源的影响更大[10, p.2]。这一观点的流行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普遍意义上的科学特别是技术,首次同时成为知识界和大众社会进步观念的中心。18、19世纪的先进发明带来了工业革命,似乎暗示技术可以也将会解决所有的问题(虽然技术开始创造出新的问题)。
基于Thomas J. Misa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决定论的区分[8],现代批评家,有时候会将技术决定论,分为“硬性”和“软性”的版本,“软性”版本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混合了社会的接受或排斥,使其受到社会可塑性的影响。而“硬性”的版本认为技术是自主的不受社会干预的影响文化的。后一种形式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在直觉上感觉很怪异,但即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硬性”的决定论仍然闪烁着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光芒:发明和工业已经使日常生活有了可以衡量的改善,这其中就包括了比如蒸汽机车和电力这样的发明。特别是在美国,机械的创新和“技术官僚”式的思维,成为了国家、自然和宗教这些概念之外,另一个象征进步的指标。
1.1 媒体生态学(Media Ecology)
到了20世纪中期,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即使政府和工业界对科技的投资不断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以及原子能的出现导致了人们几乎一夜之间对技术的内在的社会效益产生了质疑。对我们来讲遗憾的是这正好赶上本世纪最著名的技术决定论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开始发表他关于媒体塑造人类感觉和意识相关研究的时期。
麦克卢汉的著作很复杂也很难懂,因此他的作品更多的成为文化模因而非媒体哲学,而这位思想家在20世纪60年代自己作为媒体名人的身份令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包括他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的客串,以及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但他的哲学内核是相当简单易懂的:麦克卢汉认为媒体是“人类身体及心灵的延伸”,也就是说,它们是影响人们感知、理解和联系世界的方式[7, p. 93.]。这一思想通过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广为人知,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说明媒介的属性,而并非它的“载荷”,是更加值得研究的目标。麦克卢汉的立场是较为极端的一类:对他来说,电视节目或报纸中的故事,远不如这些媒体自身的逻辑以及他们改变人们感官和经验的方式更加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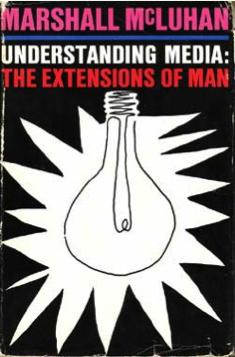
麦克卢汉的方法被他称为“媒体生态学”,这种方法运用在那些不能被称为“媒体”的技术时却有着最令人清晰的理解,至少要比我们在当代文化中使用它的时候要更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电灯泡,麦克卢汉认为电灯泡是一种媒体,因为他增强了夜间的视觉,同时也消弱了其他的感官。
虽然经常被误解成“硬性”的决定论者,但麦克卢汉实际上表达了“软性”决定论的一种非常“柔韧”的版本,在这种表达下正如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所说的那样,“技术是社会的中介和阶梯,但并非完全的驱动者”[5, p.2]。
1.2 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
媒体生态学这一概念虽然至少在媒体和文化研究中已经被人们所熟悉,但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研究人类文化如何操纵技术的领域,它从未真正的流行起来。在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s and Technology Studies - STS)领域,一种替代的观念称作“社会建构主义”,或者更为流行的说法叫SCOT——即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它倾向于用历史和人种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类是人们是如何发展并使用特定的某一种技术而非其他技术的[3]。SCOT的倡导者指出技术不是——也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作为人类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理想、目标、问题及其它的因素的反馈被创造出来的。
尽管STS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混合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但社会建构主义是上个世纪文化研究中更为广泛的趋势中的一个例子:对非物质人类行为的强烈关注甚至压倒性的关注,而对有形的物体则持不重要甚至轻视的态度,包括机器和装置及它们的创造性。例如,虽然在文学和电影研究等热门领域偶尔会考虑书籍或电影的物质构造等问题,但从事于这些领域的学者们更常提出关于媒体是如何表达人类观点、有意或无意的表达人类的意志的。用麦克卢汉的话说,文化研究只关注内容,而非媒体的属性。
1.3 空心的黑匣子
平心而论,科学与技术研究(STS)领域中的研究确实经常对科学仪器进行探究,例如STS领域的开山之作,1984年Bruno Latour对路易·巴斯德发现微生物的研究,英文题为《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法国的巴氏消毒法)[6], 但是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研究关注的是技术产生的方式,而不是事后人们对技术的反馈。这一观察形成了由Langdon Winner所展开的对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的批评,以及一种对于“软性”技术决定论的反驳[12]。正如他的评论文章的标题(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 “打开黑匣子后发现它是空的”)所表明的那样,社会构建主义的方法未能从内到外的考虑到具体技术的运作和使用——用Winner的话说,黑匣子仍然是空的。
遗憾的是,文化研究和STS方法在媒体和技术研究者中的流行,让批评家们每当开始打开和讨论具体技术的黑匣子时,就会带来天真而无理的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指责。Winner认为这种反应部分地来自于对这些批评家所偏好的的人种学和解释学方法的威胁。但另一种更简单的解释是,技术决定论的反对意见,已经成为了时髦甚至老套的说法,只要盖子被打开,这就是一个现成的答案。
将许多技术决定论的反对意见,归结于一种将任何对技术的物质构造及使用方式的关注都自动等同于“硬性”的决定论,即认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自行发生的,像潮汐一样带着人类社会浮沉的极端立场并非是完全不准确的。实际上,我们同意这样的反对意见,也接受它们,因为这些意见实际上是支持平台研究的方法的:人类在发展文化观念和人造物的过程中,与技术是相互协商的,人类自己也创造出技术作为他们对无数社会、文化、物质和历史问题的回应。如果我们认为技术是自行展现的,并单向的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那么我们至少要砍掉平台研究的一半内容:那些关于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计算机平台是如何体现特定的文化概念和理想,以及它们是如何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被创造出来的研究。
虽然硬件平台对于许多人——包括学者、公司和电子游戏玩家来说是方便或熟悉的。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平台类型,平台可以是任何的能够在其上进行进一步计算性开发的计算机系统。它既可以完全用硬件来实现,也可以完全是软件(那些可以运行在若干硬件平台中的任何一种上的软件),或者是两者的某种结合。

重要的文化产品在硬件和软件的平台上都曾经出现过。雅达利VCS是纯硬件的,由一个连内置ROM都没有的电路组成。与之相对,Java则提供了一种虚拟的计算机,它的软件实现能够运行在许多不同的硬件系统上。它被Sun公司描述为平台,做这样的思考是有用的:
平台是某种程序可以运行在其上的硬件或软件环境,比如微软Windows、Linux、Solaris OS和Mac OS。 大多数平台,可以被描述为操作系统和底层硬件的组合,Java平台与其他许多平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运行在其他基于硬件的平台之上的,纯软件的平台[11]。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平台可以包括其他平台,就像麦克卢汉的概念中媒介可以包括其他媒介一样。
如果将软件环境独立于它运行的硬件之外进行思考也是有用的,至少将运行环境视为平台是有一定意义的。特别是像那些在Java和Flash中完成数字媒体创作,这些系统被设计为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以相似的方式工作。人们会说某个东西运行在“Windows”上显示出软件是理解平台的重要视角,即使“Wintel”一词(作为“Windows”和“Intel”的组合词)也包括了硬件层面的信息。1980年代初,出版商会把各种BASIC语言程序印在书里,并且不只针对特定某种微型电脑,他们当时是把BASIC语言当做一种平台来看待的——尽管它甚至并不真的是一种编程语言,而是由一系列相似但实现方式各不相同的编程语言组成的大家族,当然平台研究的方法不应该忽视这些差异,那这些因素在考虑BASIC和其他作为平台的软件系统是可能是有用的。
家用电子游戏机是一种有影响力的、重要的平台类型,也是最容易被辨识的平台之一,因为制造商已经将这种系统的设计和功能标准化,并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广告宣传并使之与众不同。但平台在各种计算形式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苹果2这样的个人电脑是平台,而BASIC这样的编程语言也可以认为是平台。过去几十年来文化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电脑系统,比如1960年代和70年代的柏拉图(PLATO)系统也是平台。平台支撑了数字艺术、超文本、交互式小说、聊天机器人、不属于标准游戏的娱乐程序,以及其他各类新媒体的创作。

这种误解无疑部分源于平台研究系列图书选择了首个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子游戏平台雅达利VCS作为第一个研究对象。但或许也是由于电子游戏研究和其他数字媒体研究之间的普遍隔阂,它们有着不同的会议、期刊以及书架上的不同空间。我们希望平台研究丛书能够为作者和读者提供跨越这些界限的机会,而绝非是巩固这些界限。
虽然我们认为“平台”的概念不仅涵盖电子游戏系统,也不仅仅涵盖硬件,但我们仍将这一系列的研究聚焦于那些开发者们能够在上面进行创造性工作计算的(computational)或计算机(computing)系统上。我们在考虑计算平台的同时并不否认其他类型的平台——比如说石油钻井平台、铁路平台、政治平台和通信平台等等。计算平台与其他这些平台不同,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数字媒体相关工作的特定基础。当我们在定义此处“平台”的含义时,我们赞同Mosaic浏览器的联合创始人、网景公司的创始人、以及社交网站Ning的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观点:
从定义上来看,一个“平台”是一种可以由外部开发者及用户重新编程及定制化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平台原始的开发者无法考虑到或是没有时间去满足的无数需求和定位可以由此得到满足。[1]
这个定义不仅仅简明扼要的阐释了平台的概念,还解释了平台的灵活性是如何为其提供创造的潜力的。在后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2],安德森专门针对软件平台强调(原文使用了粗体字)“定义平台的关键字是‘程序的’(programmed),如果你可以给它编程,它就是平台;如果不行的话,它就不是平台。”
1.4 对计算意义的反驳
在名为《YouTube等在线内容提供商如何定位自己》(“how online content providers such as YouTube are positioning themselves,”)的分析中,传播学者Tarleton Gillespie详细地考虑了Web 2.0时代对“平台”一词的使用[Gillespie 2009]。他首先“强调了‘平台’一词曾经占有重要地位的语义学的四个领域,当“平台”开始被用作数字媒介的描述性术语时,这四种语义都曾经被运用过。”这四个领域分别是计算的、建筑的、形象的和政治的。对于第一个领域他写道:
在这样的技术语境中,平台一词的使用注定会专门地回到其计算化的定义:支持设计和运用特定的应用程序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是电脑硬件、操作系统、游戏设备、移动设备,以及数字光盘格式。
虽然相比安德森(Gillespie在文中引用了安德森的说法) 的定义宽松一些,因为它包含了数据格式,但至少描述了平台的计算意义的角色。Gillepsie将安德森的立场描述为试图“将这个词与其计算特性捆绑起来”然后得出结论:“平台之所以是平台,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允许编写和运行代码,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或销售的机会”

Gillespie表示目前“平台”的定义是宽泛的,他的观点成为相似看法修辞上的支点,在2007年一位业界名人的博客文章中定义为倒退:试图“将这个词绑回来”就像让其他人回到这个术语“曾经重要的过去”一样。
如果我们认为这只是“在线内容提供商”的公开言论的话,Gillespie对“平台”一词的看法或许是合理的,但如果他把平台的计算意义解读为过时的,这种看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无论 “平台”如何被使用,作为计算基础设施的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比如说当今的电子游戏开发者就对“平台”一词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并且他们使用“平台”一词的方式和我们以及安德森是一致的。和任何软件的开发者,包括YouTube的开发者,在他们编写软件的时候也注定熟知这个含义并使用这个术语。平台作为计算平台的含义,和今天所使用的其它含义一样是属于当代的,而且总体来说,这肯定是数字媒体历史领域最为贴切的一个含义。
1.5 平台的类型
计算平台最为清晰的情形是支持通用计算的基础系统:一台运行特定操作系统的大型主机,小型或微型计算机;某种编程语言;电子游戏机或者是手持设备。有些系统可能是通信平台,或者是非常大规模的计算系统。但这种情形未必是对计算或新媒体的平台最好的理解,因为它们并非对包括电脑程序在内的数字创造物的开发提供了主要的支持。
安德森在特别谈到软件平台(主要是在线软件平台)时指出[2]了平台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访问API“,这是最容易被创建的一种,并且是是“eBay、Paypal、谷歌搜索API(在被关闭之前)、Flickr、Delicious等所使用的方式”它们需要第三方的开发者完成很多的工作量,开发者必须要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并完成所有其他所需的工作。
第二层是“插件API“,它们允许与平台进行更深入的整合,Photoshop和Firefox是提供这种功能最有代表性的应用程序;在网站方面,Facebook是第一个重要的例子。
最终,第三层表示的是开发者可以上传代码并像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上那样直接在平台上运行的“运行环境”。安德森的Ning就是线上世界中的一个例子。安德森认为第三层平台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因为它降低了开发的壁垒并开辟了新的软件生态系统;正因如此,它们值得为之付出所需的大量的资源和努力。

在转向电子游戏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时,我们看到平台之间的其他的差异:有些平台只能在寄存器层面使用机器代码进行编程(雅达利VCS),有些则有一个小型的操作系统可供汇编程序员使用(如Intellivision),有些会在ROM中内置高级语言(如苹果II、Commodore 64和许多其他的家用计算机)。有些平台围绕着特定的输入和输出技术开发,或用于专门的用途,亦或更为通用的用途。区分平台的方法有很多,但确定的是, 最有可能成为在文化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是那些人们容易接受的、具有有趣功能并且特别受到开发者欢迎的平台。
1.6 代替“这是平台吗?”……
某个东西是不是平台的问题可能无法从它自身,得到一个有用的答案。我们可以问网页是不是一个平台——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思考局限于HTML和静态文档是如何传递的话,就可以确定它是平台。那么魔兽世界呢?第二人生呢?LambdaMOO呢?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平台,因为它们都有API。但真正的问题应当是某一系统是否具有其作为平台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当开发者认为某个事物是一个平台并加以利用时它就会是一个平台;这种活动或多或少都有文化上的趣味。与其问“它是一个平台吗?”我们不如问“这个系统上开发了哪些有趣和有影响力的东西?”以及“这个系统作为一个平台是否有独特或创新的特色?”如果一个系统是一个大型的持续性的游戏, 那么玩家的代码和表演可能是最有趣的事情,而平台层次的讨论揭示不出太多的内容。但如果一个API允许以创造性的、出乎意料的方式使用某个多玩家系统,来创造某种机制或出现了经过修改(Mod)的大型的游戏实践,那么考虑平台层面的问题可能就会非常有趣,并能够通过这些创造性的实践得到启发。

平台研究是一个将计算(从其基础的层面)与文化和创意联系起来的机会。按一些特定的计算方法来看,通信研究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无论如何,在今天通信系统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并被持续的研究。虽然数字通信系统同样值得关注,平台研究仍专注于计算平台,这是半个世纪以来计算化的数字化工作被忽视的基础部分。这种方法(以及这个系列的图书所召集的例子)创立的目的是推介这种新的类型的,针对这种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对计算机的创造性使用的核心的平台的研究。
通常,对计算机技术的讨论会回到某种技术迷信上:将计算机系统的技术细节作为其本身值得庆贺的目标。而不是理解该系统的历史、文化、和表现力。当代文化中充斥着这样的“数码迷”(gadgeteering),他们欢庆从新型数码相机传感器像素数量到预测最新款手机漂亮的外观,以及(或许不那么)新颖的功能特性。这样的态度是短视的,因为这既没有提出实用性的,也没有提出批判性的技术问题。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将技术细节的讨论斥责为不加批判的偶像崇拜。
但往往这些“技术流”(geekery)讨论的拥护者,都是从经过认真研究的技术角度出发的,其中包括了对某种系统的运作方式更加细致的理解,这通常不是能够在数字媒体文化方面的学术讨论中所发现的,后者有时会掩盖甚至误解数字媒体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认为,技术上精通的“数码迷”和技术上无知的批评家,都代表了极端的立场。除此之外的选择是存在的,它囊括了两者的积极的方面。
平台研究是关于技术细节和文化之间的联系的。在一个方向上,它接受调查平台设计的特定方面是如何影响在某个平台上完成特定的作品的——例如存在某个特定的图形模式可以让某种类型的游戏得以完成,并对开发者构成相应的吸引力。在另一个方向上,它关注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因素是如何导致平台设计者以特定的方式将系统组合在一起的。这种方法认识到,在用户体验之外,文化也完全嵌入到接口、外形以及功能、代码和平台中。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时,对技术细节的考查就非常重要,这些问题的提出不单单出于技术角度的价值,也是为了阐明技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理解平台确实涉及到技术调查,这种调查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合作进行。然而,平台研究所关注的东西并不在这一领域排斥任何新媒体学者。平台研究并不非试图取代文化研究、文学批评、界面批评方法、游戏研究、代码研究,当然也不会取代软件研究,它于上述内容是高度兼容和一致的,平台研究试图利用适当的方法来理解新媒体中曾经被忽视的那个层次。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数字媒体学者,尤其是还在接受正规教育的学者,已经到了应该更多的了解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设计和编程方式的时候了。这些知识并不一定是计算机科学家和电子工程师的知识;新媒体学者的目标是充分的理解技术,使之与文化联系起来,但并不是发明新的算法、计算机架构或硬件与软件技术。如果过分的强调这种训练,甚至可能会损害数字媒体学者的兴趣,因为他们也需要与人文科学进行深入的接触。
但是正像是认真的电影学者可能会选择学习电影制片来了解他们所选择的媒体是如何被创作的,认真的图书学者也可能会研究目录学,印刷流程及技术,以及装订和造纸是如何完成的那样,认真的数字媒体学者可能需要深入的研究软件和硬件的物质构造。在这些领域适当的教育不应将注意力放在创造新的计算机平台上,也并非要成为这些平台上专家级的开发者,而是应当知道如何对现有的技术去提出最佳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回答这些问题。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Langdon Winner认为SCOT的支持者们一直担心黑匣子的打开是由于新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相对于其他传统方法而言难以理解方法的使用,这被视为对当下的主流方法的挑战。也可能是由于方法的改变增加了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的复杂度。进行我们所说的新媒体的代码层面和平台层面的工作所需的训练并不需要计算机科学的学位,有些人在没有完成任何正式的课程的情况下,就能相当程度的掌握这些方法。但对这些层面的调查的确需要兴趣、投入和坚持和跟进; 以及使用那些新的具有挑战的思维和调查方法的意愿。
我们认为数字媒体领域最需要的,是那些将细微的文化分析带入计算机系统的学者。而对这样的学者来说,学习逻辑门、计算机架构、汇编语言或高级语言——这些计算机系统的重要课题——并不比学习精神分析或后结构主义理论更加的复杂,它们只是需要一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以不同的层次去观察数字媒体。在当下这个数字媒体领域发展的阶段,我们已经超越了数字技术教育是否有用的疑问。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层次的学者应当尝试选择的去参加相关课程,并开发新的课程,追踪那些能够扩展我们理解计算机相关内容的独立研究和项目,它们已经存在并与文化发生联系了。
平台研究调查计算机系统(平台)的软硬件的设计与这些系统上产生的创造性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游戏、数字艺术、电子文学、休闲和娱乐程序,也包括完全构建在平台之上的虚拟环境。
通过选择平台,新媒体的创作者在很多方面简化了其开发和交付的方式。他们的作品同时受到平台的支持和制约。有时候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单色的平台无法显示彩色,没有键盘的电子游戏机无法接受打字输入。但是平台与创造性制作的互动还有更微妙的方式,这可能是某种计算机语言所支持的习惯,或者是由于视频和音频硬件而带来的晶体管层面的决定。除了支持或排除某些开发方式之外,平台还会鼓励或阻碍特定类型的表达性的新媒体创作,就像Shockwave和Flash平台所表现的那样。(平台不一定是硬件。)在绘制光栅图形相关的技术中,这种区别从一次只可以绘制一条扫描线,到能够支持贴图(Tile)和精灵(Sprite)的显存系统,再到原生的三维模型功能最终变得比分辨率或颜色的深度更加的重要。当然,正如在我们讨论技术决定论时所提到的那样,平台的本身就是由文化来定位的,它受到了商业、经济、社会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完整的平台研究还会考虑平台的特殊形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种特殊形态后来是如何影响了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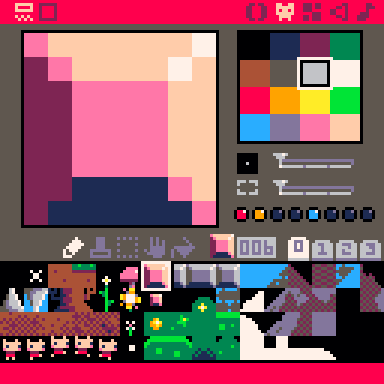
用户体验到的平台的影响是通过代码、程序的形式和行为、以及界面作为中介的。由于平台相对用户的体验来说很“深”或很“远”,要穿越若干层次才会被触及,所以它们的影响很容易被忽视,甚至于在对游戏、艺术作品或其他程序进行的细致分析中也会被忽略。并且,虽然这种影响往往是深远的,但一个平台可能会被人们不自觉地理解和假设成某种平台的形式。
特定的平台研究可能会强调技术或文化的特定侧面,并借鉴不同的批评和理论的方法,但它们应当具有技术上的严谨性和对计算系统与创意、表达和文化间互动的深入研究。虽然平台研究的书籍并不一定是由计算机科学家来编写的,而且应当面向那些没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读者,但这些书仍将深入到计算机的工作原理中去,向读者和相关的领域的参与者开启一个令人兴奋的、富有成效的新层次。
本文部分内容改编自平台研究网站文本,由Bogost,I.和N.Montfort发表于 http://platformstudies.org。
本文的英文原文可以在 http://bogost.com/downloads/bogost_montfort_dac_2009.pdf 下载
[1] Andreessen, M. 2007. Analyzing the Facebook Platform, three weeks in, http://web.archive.org/web/20071021003047/blog.pmarca.com/2007/06/analyzing_the_f.html
[2] Andreessen, M. 2007. The three kinds of platforms you meet on the Internet, http://web.archive.org/web/20071018161644/http://blog.pmarca.com/2007/09/the-three-kinds.html
[3] Barnes, B., Bloor, D., and Henry, J. 1996. Scientific Knowledg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Bogost, I and Montfort, N. 2007. Platform Studies: Computing and Creativity on the VCS, MPC, and Wii. In Proceedigns of the Digital Arts and Cultures Conference (Melbourne, Australia September 14–18).
[5] Kaplan, D.M. 2004.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Rowman & Littlefield.
[6] Latour, B. 1988.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McLuhan, M. and McLuhan, E. 1988.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8] Misa, T.J. 1988. How Machines Make History, and How Historians (and Others) Help Them Do S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13: 308-331.
[9] Montfort, N. and Bogost, I. 2009. Racing the Beam: The Atari Video Computer System. MIT Press.
[10] Smith, M.R. 1994.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in American Culture, in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Smith and Marx eds. MIT Press.
[11] Sun Microsystems. 1995. About the Java Technology, About the Java Technology
[12] Winner, L. 1993. 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8:3,362-378.